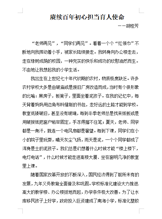弦索谈×高博文×姜啸博×王勇丨评弹半生缘:三十五载少年游
■ 编者按
1987年,上海评弹团开办上海戏曲学校评弹班,招收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学员。“87届“学员共有十人,均由老艺人带教,专业水平过硬,传统功底扎实,广受听众与道众的赞誉。三十五年匆匆而过,当初的青年演员纷纷步入中年,成为评弹界的中流砥柱。他们之中有人坚守,有人离去,有人归来,不变的是对评弹艺术如痴的热爱。
在上海戏曲学校1987届评弹班入学三十五周年之际,「弦索谈」栏目专访了“87届”铁三角: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姜啸博副团长与前上海评弹团演员、旅西华侨王勇老师,重温青葱岁月,回顾半部团史,谈谈评弹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本次访问分上下两期推送
缘起
上海评弹团87届评弹班,当时招收了出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上海初中毕业生。这一代人的童年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上海市民居住在里弄里,生活言语是吴语上海话,文娱方式依旧以听电台为主。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传统艺术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电台节目也以江南戏曲为多。幼时生活长在浓厚的吴语文化氛围里,评弹成为了三位老师成长中绕不开的元素。
高团和王老师的评弹初体验都始于电台。最早接触的是唐耿良的《三国》、张效声的《英烈》和蒋云仙的《啼笑因缘》、秦纪文的《再生缘》。十一二岁的少年基本听不太懂咿呀咿呀的弹唱,反而觉得累赘,真正“抓耳朵”的是跌宕崎岖的书情。一开始是跟着父母“有听无听瞎听听”,到后来“听听听听,听上路”,就此“上仔念头”,被评弹“钩牢”半生。
张效声在乡音书苑演出《英烈》
王勇老师回忆,当时六点半到七点半是广播书场时间,母亲欢喜听秦纪文说《孟丽君》,一家门吃夜饭辰光作背景音。“有一日说到小奸刺杀皇甫少华,橱门一开,人勿见则,那么彻底被关子吊牢!”《孟丽君》之后一档就是蒋云仙老师的《啼笑因缘》,人物和噱头极其生动,一把弦子尤为灵活。王老师特意借了张恨水的小说,提前“剧透”,但发现书情和原著还不一样,细节上的改编别有一番巧思。“这些红透江南的长篇作品符合了大众的艺术趣味,对于评弹的普及是有大功德的。”
每逢周日是评弹赏析节目《星期书会》,虽然王老师被关子吊得肚肠根痒,但是听了也觉得蛮有味道。他被节目中张鉴庭、张鉴国兄弟《花厅评理》的弦子吸引,用橡皮筋、硬纸盒自制弦子,倒也弹得出音准。1983年,王老师心肌炎住院,受一位病友影响,对琴调、薛调丰富的音乐性产生了兴味,于是借来父亲朋友的琵琶三弦,立志学习弹唱。
王勇
1984年,高博文第一次踏进四川北路的红星书场。虽然书场面积不大,但却拥有上海最早的评弹票友组织,由上海评弹团建团“十八艺人”之一的陈红霞老师指点,举办会书时常常可以请来很多名家,台下坐满了六七十岁的老听客,十四岁的高团鼓足勇气才敢进去。有赖于一身文艺积极分子的艺术细胞,他很快成为了虹口区文化馆评弹队最年轻也最优秀的票友,深得陈老师宠爱。
陈红霞
出生在评弹之家,父母都是说书先生,姜团与评弹的缘分就开始得更早了。那时交通不便,跑外码头最少大半天,有时演出前一天就要早早出发了。父母亲担心尚在冲龄的姜团一人在家不安全,往往带在码头上。小学文艺汇演,姜团和父母排练了一段短篇弹词《闪闪的红星·刀劈胡汉三》,姜团起潘冬子,父亲起胡汉三,“刀劈阿爸胡汉三”的故事在学校红极一时。
1985年,距离上海评弹团上一次招收重生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团里希望从青年中抓取一些苗子作为演员储备,是年春天开办评弹艺术培训班,面向社会上的青年爱好者开放,一周上课两次。高博文和王勇参加第一期艺训班,姜啸博加入了第二期,三兄弟在此相识,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高博文、王勇、姜啸博
幸遇
上海评弹团曾于1960年、1974年设立学馆,先后培养了两批青年演员,到了80年代中期,已都在三十朝上,亟需增添新鲜血液。改革开放后,艺术教育日益规范化。上海评弹团并非教育机构,无法颁发文凭,故而在1987年与上海戏曲学校联合开设评弹班,定向招生,校外办学,毕业包分配进团,只招应届初中毕业生。
1985年三期评弹艺训班结束,评弹班计划并未敲定,高团、姜团和王老师三兄弟各谋出路,或参加工作,或继续求学。等到1987年戏校评弹班招生时,三人都已经超龄。然而,当年艺训班的带教老师薛惠君、陆雁华两位前辈对三人印象很深,认为他们“专业思想稳定”,所以力排众议,向艺委会推荐,最终得到了陈希安、张振华等老师的认可,破格录取。遴选阶段,高博文、姜啸博和王勇三人突破初试、复试、总复试,在两千多位考生中脱颖而出,与其他七位同学一道进入上海戏曲学校评弹班学习。
上海戏曲学校87届评弹班
当时,评弹班学生们一门心思学艺,关系非常融洽,没有什么各归各的感觉,其中以三兄弟的故事最多。姜团耳音出众,乐理课听一遍旋律就可以写出五线谱了。考试时,姜团四周的位置最讨人欢喜。王老师往往占好先机:“吃不准的参考一下姜团的答案就好了!”三人还相互串门,王勇家住田林新村,高团常常跨越整座城市,从虹口四川北路骑车过去玩。姜团的父母出外码头时常不在,于是小弟兄们就一道熬夜听评弹录音。一段《许仙哭容》,板要熬过半夜十一点钟,把灯全部关掉再听才有感觉。三兄弟与刘菁、王玥等年龄相仿的同学们都天真烂漫,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就算是玩,也仅仅围绕着评弹艺术。
87届评弹班的师资力量可谓雄厚:由陆雁华、薛惠君老师担任专业班主任,戏校柯施恩老师担任文化班主任,授课老师有陈希安、江文兰、华士亭、张鉴国、吴君玉、杨德麟、张振华、赵开生、庄凤珠、杨骢等顶级大咖。为了补齐前三十年一类书“斩尾巴”形成的艺术短板,授课内容也向《玉蜻蜓》《珍珠塔》等传统书目倾斜。
薛惠君在学馆上弹奏课
三位老师提起在评弹班学习的日子都倍感侥幸:“我们是见过真神的,奶水吃得很足。本身本人喜欢,也情愿学。”由于铁三角参加过艺训班,专业上有一定基础,弹奏、伴奏方面相当质硬。其他新招的同学需要从零开始学苏州话、熟悉基本曲调和乐器,三兄弟则有小小“特权”可以不上基础课。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想着休息、离校,而是结伴在排练厅自学弹唱,像显宝一样相互分享听到的好唱段,叮叮当当夹家生。学校规定五点下课,其实三个人从来没有准点回过家,怎样样都要摒到七八点钟,乐此不疲。
回忆起和老先生们相处的日子,高团坦言:“现在的小朋友没有那么好的老师,老师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耐心。当年的老先生好像没有那么多事体。如今生活节拍太快了。很多人不断在忙,静不下心来。”
陆雁华辅导高博文与姜啸博
弹词名家华士亭先生教过评弹班《三笑》中的“追舟”与“卖身投靠”两回书。老先生上课细致至极,每每谈到人物塑造,都是引经据典、如数家珍:刘天韵如何、徐云志如何、如何安排手势眼神、甚至追舟时米田共如何摇船都有讲究。短短一回书,扩充延展开来,有无数细节和掌故值得发掘,老先生全都倾囊相授。
华士亭
“琶王”张鉴国先生教琵琶弹奏。正如不少回忆文章所言,张先生不善言辞,为人随和,上好课也不马上走,坐一歇等同学提问。三兄弟初生牛犊,胆子很大。高博文自学《红梅赞·劝降江姐》,斗胆请张鉴国老师帮忙托琵琶。高团笑说:“现在想想莫大的荣幸与幸福!”
有一次姜团学唱张调,也是琶王托的琵琶。唱完之后姜团面孔煊煊红,对王老师讲:“你去唱呢!根本不用考虑琵琶的,笃定唱!感觉适意得了!”有时旧书中的特定过门弹错,学生们也不管不顾地向琶王指出:“迭个跟录音里哪能勿一样额?”老先生丝毫没有架子:“哦哟!年数长则,忘记则哇!”
张鉴国
评话大师吴君玉先生以《武松·杀庆》一回教授说表。吴先生上课氛围轻松,带来零食,先给大家分了吃,吃好开始讲课。老先生特别擅长分析人物和场景,不经意中开始教授如何让说表营建出意境,对学生们很有启发。一次考试前,王勇说这回书经常性地节拍过快。吴君玉老师对他说:“倷勿要怕,我帮倷划翎子。要是说得忒快则,我就拿手往胸前一压,倷就慢下来。”结果果真如此,吴老师临场帮忙作弊,节拍都在路子上。
吴君玉
慈师也是严师。身为班主任,薛惠君、陆雁华两位老师对评弹班学生的行为举止、谈吐坐姿、服装打扮等生活细节都要指正提点,往往一个眼神、一句闲话,学生就晓得本人能否得体。个别小姑娘纪律不好,上课在下面讲话、做小动作,江文兰老师也会在课堂上呵斥:“苏老师要是勒浪,我还要去跟苏老师说书嘞,啥人要教唔笃呀!”
江文兰、沈伟辰、华士亭等几位老师临近退休,没有长篇码头好做,就住在团里。三兄弟在楼上大房间排练,几位老先生在楼下听到表演有什么问题,马上当当当顺着大弧梯冲上来,诲人不倦地指点。高团、姜团和王老师倒也不怕,师生间并不是“猫鼠关系”,都很自然地与老师们相处。
评弹班招生计划尚未出炉时,陆雁华老师已经给姜团写信,鼓励他不要泄气:“本身条件好,千万不要放弃,接下来总归无机会的!”这一封信陪伴姜团走过那段充满未知的迷茫岁月,不断被好好收藏着。每次想到那些恩师们,三兄弟都会感慨万千:“老先生真是惜才呀!”随着年岁上去,三人对这种心态的共情越来越深,只需看到好的苗子,就会和老先生们当年一样,千方百计地鼓舞他们好好交精进艺术,全力以赴。
陆雁华、陈希安、张振华
跟师
评弹班的学制设置非常科学:头两年基础课和文化课,第三年跟师学艺,第四年实习,出码头越做。如此四年下来,一部长篇基天性够完全掌握了。
1989年夏,结束了两年的在团学习,87届评弹班十位学员组成五档小双档,分别拜师学艺。对于先生的人选,团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习艺术,光是看看录像听听录音是不够的,一定要拜还活跃在码头上的、广受欢迎、年富力强的先生,不要拜名气响但已经不说书的先生。为了打破上海团长期“排外”的偏见,还特意安排了五档中的两档小先生拜外团的老师。
高博文、崔丽萍拜饶一尘、郑缨,学说长篇弹词《珍珠塔》。当时饶郑档是一对比较稳固的中年双档,艺术成熟、经验丰富。其中,饶一尘先生创作能力强、学养深厚,被称为上海评弹团“疑问杂症的处理者”。据高团回忆,饶先生在艺术上毫无门户之见,鼓励高团自创陈希安、赵开生、薛惠君的珠塔书路,产生了评弹界绝无仅有的“三房合一子”的美谈。陈希安、赵开生两位老师都承认与高团的师徒关系,但从体谅学生的角度出发,都没有要求高团举办正式的拜师典礼。三位恩师有时会相约一道去乡音书苑听高团说书,堪比三堂会审,“日脚难过”。各位先生的艺术各有千秋,他们的鼎力支持,使得高团的珠塔书路灵活、博采众长。
赵开生与高博文
姜啸博、王玥拜张君谋、徐雪玉,学说长篇弹词《玉蜻蜓》。姜团入门时学的就是蒋调,因而拜张徐两位先生是最合适的。姜团说,虽然码头生活艰苦,住在外面,大冷天空调都没有,厕所恶臭异常,但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温暖。师徒二人长相相像,张先生不断把学生当儿子一样相待。苏州人讲究吃食,每日两位先生为学生们烧的小菜都特别好,鸡笃蹄髈更是一绝。
姜啸博与王玥
王勇、刘菁拜张如君、刘韵若,学说长篇弹词《描金凤》。王勇老师回忆道:“恩师好像父母。”拜师典礼后,两位先生把他们叫到评弹团的小亭子里面,拿出一张纸,写了两句话:“人前显贵 人后受罪。”这是太先生刘天韵传下来的警句。张刘二位老师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点钟准时爬起来锻炼身体,吊嗓子,之后就是练唱。两位学生在码头上从来不需要做家务,刘韵若老师一手包办,边烧饭边指点。
王勇与刘菁
先生们都有一套本人的教学思路,但大多只许抄篇子,不许抄剧本。因为评弹是言语艺术,艺术呈现应该是记忆中鲜活的人物抽象,而不是一个死板的文档,正所谓“书侪勒脑子里”。因而,必须锻炼学生听会说熟、现吃现吐的能力,才能使说表生动起来。如今三位老师都认为,虽然吃新书时非常痛苦,但先生的教授方法的确让本人收获颇丰。
学校规定先生需要带学生做十只码头,实际上小先生们大多跟了不止十只。即便台上因现场节拍等缘由切掉的书,老师们也会到台下补齐。老一辈评弹艺术家用一百二十分的精神关爱小先生们,目标只要一个:希望青年人能把本人的艺术传承下去!
1991年夏天,经过四年的学艺生活,上海戏曲学校1987届评弹班举办了毕业公演,十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式成为光荣的上海评弹团团员。
上海戏曲学校87届评弹班毕业公演
危机
然而,等待这些青年的,却是不那么光明的未来。
文革以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大批忠实的评弹观众“饿听书”,纷纷选择报复性消费,演出场次和收入井喷式增长,长年受压抑的演出市场空前繁荣。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外来文化迅速走进国门,占领了文化市场。新的艺术方式盛行,消磨时间的方式越来越多,大众普遍对电视、歌舞感兴味,音乐茶座、录像厅、歌舞厅、台球馆、麻将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历了《霍元甲》《姿三四郎》《上海滩》三部电视剧,江浙沪地区的评弹长篇夜场彻底被打败,被迫关门改做日场,至今都没有恢复。弹词名家蒋云仙老师也说道:“《啼笑因缘》再火,遇到姿三四郎、霍元甲,只好甘拜下风。”
1985年蒋云仙演唱《啼笑因缘·别凤》
同时,过去喜欢听书的中高层文化消费者也发生了转变,经济建设风头正盛,民众忙着出国、读书、做生意,没有心思慢条斯理地品尝传统文化了。社会审美趣味也在转化:西厢记、珍珠塔、玉蜻蜓等传统书目不再受欢迎,接不到场子;武打书、侠客书、猎奇书大行其道。弹词演员没有办法,只好把描金凤改名徐惠兰,神弹子改名韩林传,双珠凤改名文必正,新瓶旧酒,重新包装上市。
以上种种缘由使得票价本就低廉的书场盈利能力大大降低,评弹、越剧、沪剧等传统戏曲蒙受了一系列的波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由于票房收入减少,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评弹界流失了太多拔尖的中青人才。
姜啸博
87届评弹班的学员们甫一毕业,就遭遇了空前的行业危机。年龄渐长,眼看百业兴隆的经济浪潮,面对成家立业的经济压力,不少人选择了转业。
1993年,姜啸博离开上海评弹团,改做摄影师。采访中,姜团坦言:“当时转业,我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下了很大的决心。”1994年,王勇离开上海评弹团。当时87届只剩他和高团两个男生留团。最终,王老师选择进入上海机械设备成套集团,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我从小欢喜评弹,融入了学业,当时非常痛苦煎熬。”回忆起当年的决定,他无法地说:“现实生活是骨感的,虽然转业之后收入、环境跟之前比几乎是天壤之别,但我的确做了逃兵,因而从内心深处佩服高团的坚守!”
高博文在玉兰书苑单档演出选回
我问高团:“是啥物什支撑倷走过最低潮个辰光?”
高团笑说:“谈不上忍辱负重,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时过境迁,高博文回忆起当年的评弹演员真是“既无名,又无利”。最推板的一只码头,有一天拆账两个人只拿到27块5角。“收入真个蛮低个,码头也接勿着,出访演出、电视采访,老师也很少有实梗个机会,那哼轮得着阿拉小青年呢?”九十年代的城乡差距还很大,码头上一个月下来,高团本人感觉整个人都乡气,回到上海“样样事体侪戆特则”。与此同时,高团思想负担也很重:“人家走了,本人的前途怎么办呢?”
高团也坦言,本人并不适合做生意,当时社会上出风头的、赚钱的工作都不是很如意。在团里接触的老先生比较多,不免也有点眼高手低,不想做打工仔,还是想做说书先生,终究没有狠下决心出走。
1999年高博文与余红仙、江肇焜等共同研讨中篇评弹《玉兰花开》剧本
87届的同学们都走了,团里的老师们把希望都寄托在高团身上。老先生们的关怀温暖了高团失意的内心:“遭到关注,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这不只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愈加是精神和艺术上的提携。”为着高团这份坚守的信心,老先生愈加倾其所有地教授,爱护这棵87届的独苗。
当年苏州电视台流派演唱会,各大流派的传承人都去了,陈希安老师坚持让高博文为他伴奏。在电视书场殷导的支持下,高团上台演唱了一首「珍珠塔·痛责」。赴港演出、97年香港回归演出、98年评弹研讨会,老艺人们把高博文捧得很高,让这位上海评弹团的新星出尽风头。他们苦口婆心地鼓舞高团:“评弹事业还是要承继下去个。人家走则,倷还勒海。将来风云际会个辰光,倷就会得脱颖而出。”
1999年高博文与陈希安演出《珍珠塔》
这颗老一辈评弹表演艺术家们悉心栽培的评弹青苗静静地积蓄着养分,等待未来那春风拂面的晚上。高团的好弟兄姜团和王老师虽然离开了专业院团,但走得不远,并没有放弃对评弹艺术的追求,不断与评弹藕断丝连。那时的冬眠,也许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正如老先生们所说,这一切的坚持总会有价值,聚变时辰就要来临了。
请看下期弦索谈专访推送
弦索谈×高博文×姜啸博×王勇|评弹复兴路:且将新火试新茶
采访策划
社长
文案采写
社长
音频剪辑
步心 社长
推文配图
王勇 姜啸博
版面设计
阿浩
图文校对
慕棻
听赏吴侬雅韵
传承吴语文化
品尝属于伲个江南生活
关注我们 更懂评弹